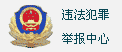○蔡赞生
春水
鸭子是春水的先知。鸭掌划动处,光的碎片在水面处跳跃——不是反射,而是新生,是水重新认识自己流动身份的仪式。浮霜相互推挤着,漂向河流深处更浓郁的蓝和暖,那暖里融化了整个大地对自由的渴望。
风从东南方来,带着海盐与泥土混合的气息。枝条开始迎兑枝条,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交换暗语;叶片轻拂叶片,窸窸窣窣诉说着什么。整片林子都在翻译同一则消息:醒来了,都醒过来了。连石头缝里的苔藓都湿润得想要眨眼——是的,春天让万物都有了眨眼的冲动,因为光不再刺目,而是温柔地邀请每双眼睛重新认识世界。
暖化的不只是河流。我感觉到胸腔里也有什么在消融、重组。那些冻僵的记忆,那些封存的情感,此刻都随着河水的流向开始松动。我把手伸进水中,触及一片清冽的觉醒。这水将汇入更大的水,将经过稻田的入口,将托起渔船的腹部,将最终抵达我三面环山的故乡。
归途
山径上的残霜退到哪里,连翘就开到哪里。金黄的花瓣像是太阳洒落的鳞片,在还料峭的风中微微颤抖。更隐蔽处,石橄榄紧贴着岩壁生长,肥厚的叶片储存着整个旱季的耐心。而半边莲——名字里就带着缺憾之美——在溪涧旁开出不对称的紫色花朵,仿佛春天也不追求完美,只追求完整的生命表达。
我沿着新修的公路行走。沥青的气味还很新鲜,像刚拆封的信笺。这条路连接起嶙峋与平缓,连接起封闭与敞开。路的尽头,家的轮廓在逆光中固执地存在着,如一座温柔的堡垒。余光中说乡愁是枚邮票,对我而言,乡愁是这条不断延伸的公路本身——它丈量着我的远离,也预设着我的归还。
父亲还在耕种。他的蓑衣在细雨中像一片移动的苔藓,紧贴着大山的肌肤。每一道田埂的曲线,都是祖先与地势谈判的结果。他开垦的不是荒山,是时间里的脉动——把被城市化遗弃的时辰,重新种上庄稼的韵律。我看他弯腰的弧度,与新芽触碰天空的弧度惊人相似。原来人与植物,都在完成同一种鞠躬,向土地,向生长,向周而复始的承诺。
家是什么?是屋顶的瓦片在春雨中渐深的颜色,是灶膛里柴火噼啪的方言,是堂屋门槛被岁月磨出的弧度。更是父亲不肯离开的三亩田园,是母亲腌制的咸菜在陶瓮里发酵的耐心。我曾在钢筋丛林里寻找意义,直到看见父亲从荒山中收获的一筐番薯——它们沾着新鲜的泥土,像刚出土的答案。
黄昏时,我站在半山腰回望。灯火次第亮起,每盏灯都是一个坐标。山岚开始缠绕村庄,像时光的纱巾。我突然明白:家的意义不在于返回,而在于你始终知道自己可以返回。就像春天年年来临,不是因为它从未离开,而是因为它离开时,已把归途写进万物的年轮。
呼唤
禾雀花是春天最大胆的隐喻。它们悬挂在山路边,每一朵都像展翅欲飞的翠鸟,却被细细的花梗拴在藤蔓上。但最惊人的不是形态,是它们相爱的方式,一株极不安分地试图进入另一株里。不是纠缠,是融合;不是依偎,是生成。生物老师说这是传粉的需要,但山民们说,看,连花都知道要找到另一半才能完整。
我在这片绿意中迷路了,山路诱惑我走向更深的春天。云海正在生成,从山谷里蒸腾而起,依偎着大山的轮廓,像一场缓慢而盛大的拥抱。松针的新绿与旧绿层层叠叠,绘出时间本身的剖面图。风经过时,整座山都在轻轻晃动,不是摇晃,是荡漾。春山如舟,载着所有苏醒的生命驶向盛夏的港口。
成为春天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?是允许融霜渗入我的血脉,让心跳与解冻的节奏同步;是学习野山菊,在贫瘠处也能捧出金黄;是理解禾雀花,勇敢地打开自己迎接另一朵花的进入;是羡慕父亲,能把一生过成一场与土地的持久对话。
我找到一块被阳光烘暖的石头坐下。地气透过石头的孔隙传递上来,那是大地的心跳。闭眼时,能听见无数细微的声响,根须汲水,花苞拆封,昆虫振翅,露珠滚落。
黄昏降临前,我朝着山谷呼喊。没有回声,只有更深的寂静包裹过来。但这寂静是丰盈的,充满即将破土而生的承诺。起身时,衣襟沾了几片花瓣。我没有拂去。就让这片春天的证据陪我走过吧。毕竟我们都在渡往某处,春天渡往盛夏,溪流渡往海洋,而我,正沿着这条开满野花的小径,渡往生命下一个适时的位置。
风又起了,这次它捎来了家的潮润。我知道,那是海在呼唤所有属于水的,山在呼唤所有属于土的,而春天在呼唤所有不曾忘记生长的。






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
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