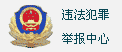○蔡赞生
我总在思忖,需耗尽几篓上好的松烟墨,磨秃几管狼毫笔,才能以水墨的浓淡,勾勒点染出这座古戏台全部的沧桑与沉浮?那梁柱间的每一道擦痕,都隐藏着一折不为人知的离合与悲欢。
鼓声响起,须得在太阳下山之时。看那青霭如薄纱般缓缓隐退,整个村庄素净、恬淡得像一张徐徐铺展的未染宣纸,等待着故事的降临。归巢的鸟雀簌簌地敛起羽翅,不经意间,从翎毛的末梢抖落下最后一缕鎏金般的夕光,为这动感的画卷点上灵动的高光。
谁说风是无形无影,最难描摹的?我早已在画中,以飞白之笔,绘出了那面鼓荡着七丈豪情与落寞的旌旗;连同那一缕从远处屋瓦间升起的、心神不定的篆字形炊烟,它袅袅娜娜,仿佛也带着欲说还休的心事。
我当然知道,即便再清亮的蟾光,亦有它照不见的苔痕与暗角。戏台之下,多少年的俯仰揖让,任是谁,都已被岁月消磨得憔悴不堪。有时想来,我们那大把大把的韶华,其存在的意义,或许原本就是用来“浪费”在这些看似无用的、极致的美与感伤之上的。
于是,目光便再次投向那逼仄之地。但见凤冠压鬓,霞帔垂落如流云,点翠头面在灯下映出海棠般的光晕。水袖一甩,流波宛转,那胭脂在眼角淡淡洇开,便染就了整座春山的眉黛。
满座的观者,或许都与我一样,屏息凝神,并非只在看戏,而是在共同摹画着那眉目间的万种生情,装扮着那场遥不可及的鸾凤和鸣。
青衣敛袂时的哀怨,或花旦移莲步时的娇态,都在那泛黄脆弱的脚本页间低徊、萦绕。
直至一声“良人归来”的正字戏唱腔,清越激扬,荡开百年尘埃,直直撞入心头,余音绕梁……
看陆丰正字戏《三岔口》
戏台上,一柱光。
只有一柱光,孤悬于顶,并未完全落下,仿佛悬着的一颗心。陡然间,明晃晃的刀锋自我的脸颊闪过,一道寒光,带着金属的冷意。静极之中,似乎能听见蛛丝断裂的细微声响——那是平衡被打破,危机降临的预告。
人生如戏,大多数时候,我们何尝不也隐藏了自己?在迎来送往的世故里,那无形的危机,总如影随形,步步紧逼。
风,是唯一的旁观者,它匍匐在虚拟的店门之外。夜,谜一样难解,布满了绕不开的搜寻与试探。
这三岔路口,汇聚了世间所有不可测的人与事,命运在此分合。我时常恍惚:如果舞台上,黑的角色是我,那么那个白的,执意要与我周旋到底的,在生活的镜像中,又会是谁?
但见台上人,闪躲腾挪,身姿滑溜如琉璃。那干净利落的身手之下,无人能窥见我(抑或是他?)内心深处的疲惫与千钧重负。这宿命的来处,仿佛延伸自一条精神的古道,穿过内心的荒原与狭谷,直抵那战马嘶鸣、充满传奇与禁锢的沙门岛。
于是,只能把脚步放得轻了,再轻一些。尽量不去惊动每一撮积年的墙灰,仿佛那扬起的尘埃,便是过往的罪证。每一步,都须步步为营;每一步,皆是步步惊心。
在这极致的静默与紧张中,我已分不清那四起的风声,究竟来自舞台的墙外,来自对手的喘息,还是来自我自己的胸膛之内——那是我另一重,连自己都感到陌生与恐惧的面相。






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
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