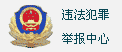○蔡良进
二十年戎马,“八一”总在心头。那不是日历上的红圈,是二十个春秋里,从未褪色的滚烫 —— 像钢枪的寒光,像军徽的灼热,在每一次心跳里叩响,如同一记记归营的军号,总在梦回时扯着心尖往营区的方向走。
钢枪磨出掌纹,那纹路里藏着的,哪里是老茧?是界碑的坐标,是巡逻路的碎石,是千百次举枪时,准星里定格的万家灯火。掌心的沟壑深了,像幅揉皱又展平的地图,每道褶皱里都嵌着不舍 —— 舍不得把枪交到新兵手里时,那声带着颤音的 “保重”;舍不得最后一次擦枪时,枪管映出的自己,两鬓已生了霜。可握住的 “守护” 却越来越沉,沉得像身后的山河,一草一木都在掌纹里生了根,成了走多远都忘不掉的牵挂。连指节间偶尔摩挲的军功章,都在这些纹路里找到了契合的弧度 —— 那枚章的棱角早被磨得温润,背面刻着的年份却依旧清晰,像那年山洪里泡皱的指腹,像那年雪灾里冻裂的唇角,每一道磨损都是一次冲锋的印记,也是一串系在心上的铃铛,稍一碰就响出训练场的番号声。
军装浸着汗渍,那盐霜里晒过的,哪里是暑气?是演训场的尘土,是暴雨中的泥浆,是寒夜里岗亭上,凝结又融化的霜花。衣料磨薄了,像层贴在骨头上的皮肤,脱下来时总带着股硝烟与阳光混合的味道,那是比任何香水都让人安心的气息。可裹着的 “滚烫” 却越来越烈,烈得像胸腔里的火,烧过二十载晨昏,依然能点燃每一次冲锋的号角。军功章别在胸前时,总像一块吸饱了汗的铁,凉丝丝地贴着皮肉,却烫得人想起庆功宴上没说出口的话 —— 那枚章该分一半给牺牲的班长,分一半给替他挡过弹片的战友,分一半给永远守在界碑下的无名石头。如今隔着抽屉摸到它,还能想起第一次戴上它时,班长拍着自己肩膀说 “这是军营给你的回信”,那封信,至今还在心头拆了又拆。
都说岁月会磨平棱角,可这双手,仍能在紧急集合的哨声里,三秒扣紧武装带;这身衣,仍能在硝烟未散的演练场,瞬间挺成钢铁的墙。连那枚军功章,在抽屉里与木棱相触,叩出的轻响,都像半截未吹完的军号余韵,低低唤着 “稍息”“立正”。那声响里裹着旧时光的温度,唤出二十年前那个攥着入伍通知书的少年,眼里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—— 那光像营区不灭的夜哨灯火,亮着多少回梦里回营的热望;而对军号与迷彩的眷恋,早像藤蔓缠上了心尖,每一次呼吸都能触到那带着硝烟味的牵挂。
“八一”总在心头,是因为它从不是一个符号。是新兵连第一次敬礼时,帽檐下的热泪;是退伍时叠成豆腐块的被角,压着的不舍;是如今每次听见军号,脊梁骨下意识挺直的本能。而军功章不过是这一切的注脚 —— 它会蒙尘,会氧化,可背后那些被守护过的黎明、被接住的黄昏,早成了比金属更坚硬的勋章,嵌进了骨头缝里。就像退伍那天,连长塞给我的那枚领花,至今还在衬衣袖口磨出的痕迹里,闪着 “常回来看看” 的光。
二十年戎马,磨老了少年鬓角,却磨亮了骨子里的光。那光里,有掌纹里的山河,有汗渍里的星辰,有“八一”两个字刻下的滚烫,还有军功章压在心头的重量 —— 那重量里,从来不止荣誉,是 “不退” 二字,写了整整二十年。而那份眷恋,早已化作血管里的密码,每次心跳都在默念:我的军营,我的钢枪,我从未离开。






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
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