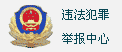◎蔡良进

观音岭一景。
沈绿洋 摄
观音岭的花岗岩阶,是大地写给沧海的手札,页脚浸着百年咸潮的余韵。清光绪年重修的石板,被岁月磨出了暖润包浆,宽狭交错的纹路里,嵌着四百五十五公里海岸线的喁喁私语。潮声从碣石湾深处漫来,不似奔涌的狂歌,是缠缠叠叠的浸润——从石阶第一级起,逐寸漫过苔斑的褶皱,漫过“永镇安澜”的刻痕,漫过行人遗落的、带着咸腥的足音。风掠石面,岁月与浪涛便在纹路里相拥,淌出细碎绵长的和鸣,缠上每一寸石肌。
海风裹着细盐,一遍遍吻平石阶的棱角,把坚硬磨成了温柔的妥协。浪涛洗亮的清晨,潮声总最先苏醒,轻叩石板时带着沙粒的脆响,像老艺人手中浸过岁月的簧片,在时光里悠悠震颤。石阶旁的摩崖石刻默立百年,杨文广拔剑止水的传说,被潮声翻来覆去唱着;俞大猷题刻的“镇海石”,在朝潮暮汐的叩问中,愈显骨力苍劲。潮声从不是过客,它是石阶的年轮,每一圈都刻着山海相依的契约。潮来潮去,石面纹路又深一分,将山海故事妥帖藏进肌理,不与外人言说,只等风与潮轻轻唤醒。
石阶曲曲弯弯,牵向旧时古官道,曾是连通碣石卫的要道,车马喧嚣、人声鼎沸漫过石面,如今只剩风与潮,在此处缠绵流连。常有白发老人坐于中段平台,指尖摩挲着磨得发亮的贝壳,潮声漫过他的衣摆,也漫过记忆里鲜活的渔汛。幼时跟着阿公赶海的光景仍在眼前:退潮后的石阶缝隙,藏着乱窜的小蟹、饱满的花蛤,潮声一紧,便是炊烟升起的信号。袅袅烟火从石阶顶端的村落漫开,与海的咸腥缠成一团,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人间踏实。而今潮声未改,石阶却载着岁月沉了下来,把过往的繁华与喧嚣,都酿成唇齿间低低的絮语,这絮语随潮声漫开,一路淌向品清湖的暮色里。
暮色携着观音岭传来的潮声余韵,把海面铺成流动的锦缎。渔船归港的汽笛掠过水面,与浪涛撞个满怀,漫过来的潮水里,混着蚝烙的焦香、老铺擂茶的醇厚,漫着汕尾最地道的烟火气。有人踏着潮声拾级而下,鞋底蹭过石板的声响,是潮曲里最鲜活的注脚;有人凭栏远望,潮声漫过眼眸,把一眶乡愁揉进粼粼波光,随浪涛轻轻晃荡,晃成心底最软的牵挂,落进岁月深处。
雨落时,潮声便添了几分绵长,像扯不断的时光丝线。雨水顺着石阶纹路漫淌,与涌上来的海水相融,分不清哪滴是天的温柔,哪滴是海的深情,只把石面浸得愈发温润。古官道的石板被冲刷得透亮,苔痕愈显鲜绿,像大地不慎漏下的星光,缀在石面,藏着细碎欢喜。潮声漫过石阶,也漫过时光的边界,让远古的传说与当下的烟火,在方寸石面上共生共息。石缝里藏着的旧事,被潮声轻轻唤醒,又悄悄珍藏,在山海间一遍遍轮回,成了岁月最动人的回响,绕着石阶久久不散。
深夜的潮声是软的,像母亲耳畔的絮语,漫过沉睡的石阶,漫过“周恩来同志渡海处”的纪念碑,漫过汕尾人滚烫的初心。黄旭华心底藏着的潮声,是深海之下无声的担当,藏着家国大义;渔民枕畔的潮声,是岁月安然的期许,裹着烟火日常。石阶向来不语,却把所有悲欢故事、赤子情怀,都妥帖托付给潮声——每一次漫过,都是时光的回响;每一次退去,都留着岁月的余温,在寂静中滋养着这片土地的筋骨与魂魄。
晨光再漫上石阶时,潮声已退了又来,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约定。石板上的水渍慢慢蒸发,只留盐粒凝成的微光,是潮声吻过的痕迹,闪着岁月的光泽。山海依旧,石阶如旧,唯有潮声永远新鲜,漫过岁月,漫过人心,漫成汕尾最动人的底色。这漫过石阶的潮声,是大地的呼吸,是时光的歌谣,是这片土地刻在骨血里、永不褪色的深情。风过处,潮声又起,漫过石面,漫过街巷,也漫过每个汕尾人的心头,在朝暮流转中,织就一幅山海长卷。






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
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